在《霸王別姬》的4個角色中,你會是誰?
全文共4000字,幫助你理解《霸王別姬》中的人物性格和象征。
"它開啟了一個新時代,標志了兩岸三地的影人再度匯聚"電影學者戴錦華如此評價這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影片,該片也是中國首部獲得法國戛納電影節最高獎項金棕櫚獎的影片,它就是華語電影山巔上的明珠《霸王別姬》
它幾乎在一部戲劇中,濃縮了所有人的影子,每個人都能在各個人物當中找到自己現在或過去的一部分。
從程蝶衣最初對于理想的一始而終,到袁四爺的逐漸妥協,再到菊仙將自己完全融入世俗生活,到最后段小樓的隨波逐流。我們或多或少都在某個階段中徘徊著,掙扎著,妥協著,亦堅持著。

真虞姬 程蝶衣
如果說程蝶衣的戲夢人生是一場悲劇的話,那么這個悲劇理由只有一個:他對理想的一始而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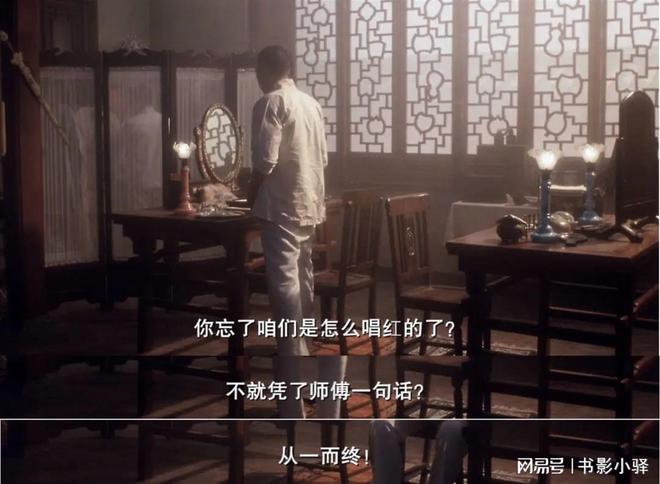
很多人會說這是一個關于愛情或者同性戀的題材,不可否認這的確是一個角度,但這種解讀很容易把人物的內在性格抹殺掉。
在程蝶衣的悲劇中在他的生命中有三個重要的階段,而這三個階段都是有關于閹割的隱喻的。
1.三次閹割
一是由于天生生有六指無法進入戲院,被媽媽狠心砍去一指,而多余的一指就代表著男性身份的閹割,這是生理意義上的,在心理上,他仍舊認為自己是一個男子漢。
他在戲劇中屢次把思凡中的"我本是女嬌娥,又不是男兒郎"錯唱為

而當他真正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是在小石頭將煙筒插進了自己嘴里,這里不用太引述弗洛伊德的性別象征理論,這徹底摧毀了他的性別認同,是象征意義上的閹割。

而在張公公那兒被凌辱,批頭散發地出來之后,他領養了一個石臺上被拋棄的孩子,也可以看作是完成了到女性/母親身份的轉變,他完成了對自我心理上的閹割。
在這時,他終于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身份,并且將這一身份視為自己存在的證明,他將表演,表演虞姬這一角色視作自己的全部人生價值。
所以,段小樓才會在屢次說程蝶衣是不瘋魔,不成活,他的一生都和虞姬牢牢捆綁在了一起
2.蝶衣的死
程蝶衣最后選擇死亡,其實是他夢碎的時刻,他突然意識到了自己回不去了,因為京劇已經沒落了
這個伏筆其實從一開始就埋下了,從賴子的死,背后的墻倒塌,到師傅的死,京劇戲班的離散。
而伴隨著京劇的沒落,是自我身份的迷失。
他在真實的世界中也扮演了一個只有在戲劇中才存在的人物:虞姬
但師哥的背叛,京劇的消沉,時代的改變都讓他深深感到自己再也兌現不了當初的承諾
而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,是師哥最后的一句話,讓他認清了:

是啊,程蝶衣一直扮演著不屬于自己的人生,他始終以為自己別無選擇,但在這個時刻,他突然意識到了自己其實是有選擇的:他學著戲劇中虞姬的命運那般,自刎而終。
他的一生就像金魚缸里的金魚,雖然非常美麗,但也只能在玻璃缸里到處碰壁。
他真正實踐了從一而終的藝術理想。
假霸王 段小樓
段小樓可以看作是整場電影的核心矛盾點,霸王別姬的編劇執導蘆薈也說,這是一部關于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之間的故事,而這個男人就在兩個女人的拉扯中逐漸走向生命的邊緣。
在他的身上,最能看出時代的烙印,對于程蝶衣來說,時代并無法在他身上刻下痕跡,只要有京劇可以表演,他就可以活下去,他可以不去管生活中的所有變化,他的心中沒有民族情懷,沒有反革命分子,沒有勞動人民,只有京劇,他就是這么一個純粹的人。
但段小樓不行,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或者說生活在生活里的人。
他身上有著極復雜的家國情懷,當他得知蝶衣給日本人表演來救出自己時,非但沒有任何感激,反而厭惡的啐了他一口,但他又看不起那些愛國青年,他諷刺鬧事的學生:

他在戲劇中是英勇畏懼的楚霸王,但是在生活中他知道自己只是一個戲子,處處陪笑,在危機時刻他想到的不是奮起抗爭,而是回歸到兒童記憶中那種自殘般的把戲。
而段小樓的毀滅也同樣可以從兩個方面說起
1.兩個女人
如果說程蝶衣所代表的是理想世界和藝術世界對段小樓的拉扯,那么菊仙則代表的是世俗世界和情感世界對他的爭奪,這兩者之間的不可協調性共同導致了他走向毀滅。
成蝶衣希望他成為自己心目中的霸王,片刻都不能展現脆弱的痕跡,不僅在戲劇中,在生活中也要從一而終。
而菊仙則堅持將小樓拉回現實中,可能是她在風塵中的一些見識讓她見慣了人聚人散,世事無常,在她眼里,小樓不可能一直是那個霸王,她希望他回到家庭,好好過日子。

兩個人其實都發自內心的愛小樓,只不過,一個愛得純粹,一個愛得卑微。
又或許,兩個人愛得也不是段小樓,菊仙愛的是家庭帶給自己的安定和一個自己不再是風塵女子的依靠。
程蝶衣愛的是那個在舞臺上英姿颯爽,威嚴赫發,說一不二的楚霸王。
2.三次拍磚
第一次拍磚是在起哄的小流氓亂場時,他作為大師兄挺身而出,將半真半價的板磚拍上自己的頭,挽回了場面

但在回去之后,師傅卻狠狠打了他一頓,罵他這是下三濫的路子,但他早就練就了一副金剛不壞之軀,他雖然嘴里極力地喊叫著,但心里早就認定
真的到了關鍵時候,做人比做事重要。
這也為他最后的背叛埋下了伏筆。
而到了第二次拍磚的時候,是在八大胡同,為菊仙解場的時候,他謊稱自己和菊仙已經訂了婚,希望各方給自己一個面子。
但各方都是來找了樂子的,憑什么給你一個戲子面子,于是他又拿出了自己的絕活。
將茶壺拍上了自己的腦袋,轉移了注意力,于是,矛盾暫時緩解了,他也因此如愿娶到了菊仙。

他的心中認定
要是活著也瘋魔,在這塵世間,在這凡人堆里,可怎么活。
如果說前兩次只是玩笑般的打鬧,這第三次他撞上的是現實的硬壁,現實它可不像道具般的磚頭,也不像自我中空般的茶壺,現實它,它太硬了,足以把任何人都撞得頭破血流。
段小樓終于認識到了,自己只是一個戲子,在時代面前,根本不值一提。
“段小樓,你不一直是霸王嗎?”
“不……不是,那都是戲,不是真的……”

于是,他拋棄了所有的尊嚴和底線,出賣了兩個最愛他的"女人",來換取自己的一線生機。
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那個為了小豆子可以挺身而出,可以沖著袁四爺說霸王就是走五步的小石頭了,也不是那個可以讓菊仙放心地從樓頂飛撲而下的依靠了。
他成了一個世故且圓滑的平庸的中年人。
世俗之嘆 菊仙
菊仙的一生可以說也是一場悲劇,或者說另一場悲劇,她摯愛著段小樓,從一開始也只是有著最樸素的愿望,老老實實的活下去,但最終,她這點卑微的如夜晚隱隱滅滅的火燭般的要求也不可實現,被熄滅在漫長的時光中,一縷青煙。
她的存在反應的是另一個截然相反的"程蝶衣",她也做到了從一而終,只不過是對世俗生活的從一而終。
她出身在花滿樓,卻對著愛情有著最純粹的向往,她無時無刻不想把段小樓拉回世俗生活中,要和京劇撇清關系。

在她的心目中,最重要的就是段小樓,或者說家庭和安全感,而在她和小樓的孩子由于在一場和國民黨士兵的吵斗中夭折之后,其實就已經注定了悲劇的發生。
在菊仙身上我們看到了太多的嘆息。
程蝶衣和菊仙之間的關系其實很矛盾,互相憎惡著,厭恨著,排斥著對方但又相互同情著,理解著,支持著。
在程蝶衣最脆弱的兩個時刻:生病和被小樓拋棄時,都是菊衣在他身邊,默默地心疼著他。

甚至我覺得,程蝶衣其實是隱隱的嫉妒菊仙的,他嫉妒菊仙真實的女性身份,他嫉妒她可以讓自己心目中的霸王俯首帖耳
所以,在批斗大會上,程蝶衣并沒有檢舉段小樓,而是將所有怒氣和指責都發泄在了菊仙身上,他將一切的過錯都怪罪于菊仙,但他又何嘗不是在對自己發泄呢?
在最后被批斗、被程蝶衣揭發之后,菊仙無法忍受段小樓的背叛,決定自殺,臨走之前她將劍默默還給了程蝶衣,便轉頭離開了,她的眼神中沒有恨,只有一種自憐式的悲憫和原諒。

亦正亦邪 袁四爺
其實恐怕很多人都沒有看到袁四爺,他似乎總是隱隱的徘徊在整場戲劇的邊緣,起到些不痛不癢的作用,但袁四爺其實是一個必不可少的人物,在他的身上,重疊著一種矛盾性。
他雖然身處世俗當中,卻對最純粹的美有著最極致的追求,他對于紅塵中的男男女女有著極強的厭惡。

但程蝶衣的出現讓他看到了自己理想實現的可能,一種完全不沾染世俗,干凈的氣質
他將自己身上無法實現的愿望投射到了程蝶衣身上。
他在法庭上他為程蝶衣做辯護的時候,也是在為京劇做辯護,他憤怒檢察官將京劇中的國粹比做污言穢語,他更憤怒在這個時代沒有人能理解程蝶衣的美。

其實還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是,袁四爺,段小樓和程蝶衣之間也形成了一個三角戀。
而袁四爺只有在扮上霸王的時候,才能惹得蝶衣動情,在這段關系中,袁四爺被符號化了,成了一種代償
他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彌補了段小樓身上沒有的東西:對于純粹的美的追求,即使在最后審判被處以死刑的時候,他還想要走臺步下場,維持自己最后的尊嚴,也是一個活在戲里的人。

但他的身份又使得這一切成為泡影,在影片中,他的定位會更偏向于一個剝削百姓的地主角色,包括從最后人民審判中也可以看出他平日里作惡多端,很不得民心
他在亂世中左右逢迎,兩面討好,他不屬于楚霸王式的英雄人物,也不是那種可以站在時代浪潮中一呼百應的人,這些都賦予了他很多小人物的特征,他卑微,茍且又純粹,這兩種極端性格疊加在一起,造就了這亦正亦邪的袁四爺。
但如果少了他,其實程蝶衣和菊仙都無法直視對方,如果說程蝶衣和菊仙都在對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,那么袁四爺就是那面顯示雙方的鏡子,給了一個緩沖,一個理解的空間。
寫在最后
其實關于這部影片還有許許多多能說的話,包括三贈配劍,小癩子的死,戲曲霸王別姬的含義等等,但我認為這些都不是能讓霸王別姬在29年后仍能俘獲一代代觀眾的原因。
恐怕沒有比霸王別姬更出名的國語電影了,即使到了29年之后的今天,仍有無數人,無數影評分析將目光聚焦在它身上。
它身上包含著太多的可能性,它讓你知道好的悲劇標準是什么:你看后不知道該恨誰,只留下一聲嘆息。如別林斯基所說:“偶然性在悲劇中是沒有一席之地的。
每個人似乎都有著自己選擇,但每個人都又似乎走上了自己固定的宿命
聲明: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容,如無特殊說明或標注,均為采集網絡資源。如若本站內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益,可聯系本站刪除。
